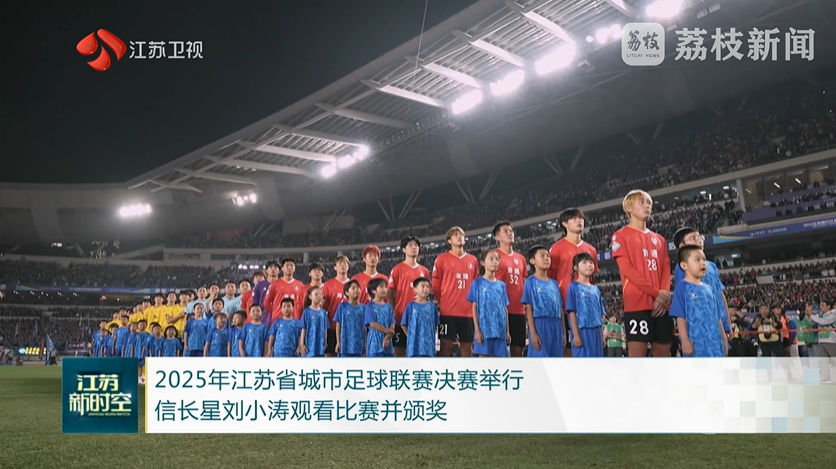人物简介
李飞,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创新药物转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药学会药物化学分委会副主任委员,苏州缘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长期从事脑保护、神经病理性疼痛等相关创新药物研究。授权中国发明专利30余项,PCT发明专利2项。研究成果发表于《Nature Medicine》等学术期刊,主编药物化学、药物化学实验等本科教材3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参与重大、重点项目各1项。曾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 本报记者 蒋明睿
“我不是顶尖的科学家,也不是顶尖的企业家,但或许我是在企业家里比较好的科学家,科学家里比较好的企业家。”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苏州缘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飞这样调侃自己。
虽已进入花甲之年,展望未来,他仍怀揣着带领一个初创企业腾飞的梦想。他研发的脑卒中候选药物ZL006-05已完成Ⅲ期临床研究,有望填补全球医学空白,“沉睡多年”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候选药物YJ2301也进入临床前研究。
过去40年,从学校到企业再回到科研岗位,最终走上创业之路,在一次次转型中,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创新梦”。
不甘平庸的“任性”转身
1985年,李飞从苏州大学化学系毕业,被分配到南京一所中专做老师。日子波澜不惊,但内心深处,他对挑战的渴望日渐滋长。1992年,李飞毅然考研,考入中国药科大学,开启人生第一次重要转身。
1995年硕士毕业后,他进入南京生命能科技开发公司,投身当时方兴未艾的仿制药领域。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李飞很快因出色工作能力晋升为总经理。
“那个年代做仿制药,技术门槛相对不高,关键是要有对市场的正确判断。”当时,仿制药市场一度陷入“国外新药一出,国内几十家蜂拥”的低水平混战。李飞深刻体会到其中的无序与局限:“仿制药物化合物结构明确,合成工艺可优化,我们甚至能做得更好,但这终究是在‘抄作业’。”
一次,他精心研发一年有余的抗脑卒中仿制药,在送审时发现竟有百余家同行竞争,前期投入付诸东流。“很多企业做仿制药是踩着底线走,这不是好趋势。”他清醒认识到,“只有创新药,才有前途。”但当时的药企创新能力普遍不足,甚至对于一些候选药物是否具备临床价值都缺乏准确判断力。创新能力的匮乏,创新药物面临巨大的风险,导致国内大部分药企只能在仿制药物领域“内卷”。
“我这个人一直比较任性,觉得没有挑战了,就想‘出走’。”2002年,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成立,李飞凭借高级工程师的身份获聘副教授。他再一次“转身”,回归学术象牙塔。李飞此次目标明确:只做技术壁垒极高、全国仅一两家能做的“高精尖”仿制药。这对他而言并非难事,至2005年左右他成功开发出五六个仿制药,并借此积累了宝贵的科研启动资金——100万元。这“第一桶金”,为他日后叩响“创新之门”埋下伏笔。
“创新梦”让他站在世界前沿
他想做创新药的念头始终没有消失,可找到方向何其艰难。环顾国内,彼时许多所谓“创新”,不过是在国外一些已知靶标和药物结构上做些修饰,意义有限。真正的源头创新,路在何方?
创新药物的终极目标是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李飞将目光聚焦到脑卒中患者,这类患者存在“4小时黄金抢救时间窗”,但大部分患者难以在4小时内获得对症治疗,有没有药物能延长这个治疗时间窗?如果超过这个治疗时间窗,有没有药物能够减轻损伤?
关于脑卒中的病理机制已有充分研究,李飞团队选择用“返璞归真”方式思考问题:脑卒中后大脑发生了什么?简单来讲,大脑中存在兴奋性神经递质和抑制性神经递质,两者达到平衡,就能维护正常的生理功能。脑卒中发生后,兴奋性神经递质过度释放,通过一系列信号通路,产生有害物质损害脑组织。以往的药物研发方向主要考虑如何清除有害物质,疗效有限。李飞团队则想从“因”入手,直接抑制有害物质的产生。
团队历经近两年的艰苦实验,进行无数次筛选与验证,终于发现了一条关键的特异性蛋白信号通路,并成功证明了干预该通路能有效阻断有害物质产生。这一重要科研发现,为脑卒中治疗提供全新思路。然而,从靶点通路到发现一个真正的药物分子,其间的鸿沟深不可测。发现只是长征第一步。
再经过近两年的持续攻关,他们成功找到作用于这条关键信号通路的全新靶点,并筛选、设计出能有效调控该靶点的化合物ZL006。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因其创新性和潜在价值获得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的认可——2010年,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Nature》杂志子刊。这不仅是南京医科大学校史上首次在Nature系列期刊上发表论文,更标志着李飞团队在脑卒中创新药研发领域,已经站在了世界前沿。
通过对ZL006的进一步结构修饰,终于获得了药效更好的候选药物ZL006-05:动物模型中ZL006-05的脑保护作用明显优于阳性对照药依达拉奉,还能显著缓解脑卒中后的抑郁症状。ZL006-05作为具有全新作用机制、全新化学结构的First-in-Class创新药物,为伴抑郁症的脑卒中患者的药物治疗提供更好的选择。ZL006-05专利成果以5000万元转让给先声药业,交由先声旗下子公司南京宁丹新药全力推进后续开发。目前,ZL006-05的Ⅲ期临床试验已圆满结束。
未竟征途里“缘聚”启航
ZL006-05的转化开发告一段落,李飞又操心起团队持续10余年优选出的化合物YJ-2301。YJ-2301具有优异的神经病理性疼痛镇痛作用,具有全新作用机制,没有一线药物普瑞巴林等存在的嗜睡、多次给药耐受等缺陷,一旦研发成功,将和现有临床药物形成差异化竞争,市场空间巨大。然而,新的靶点虽然具有更好的创新性,同时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面对技术难题和看不到底的研发经费,项目陷入了瓶颈。
科学家的理想与市场的现实,在此时形成了尖锐的碰撞:高校擅长基础研究和早期探索,却无力承担后续动辄数亿元的完整药效评价和产业化推进;药企则需要看到更明确、更低风险的后期数据才敢重金投入。这中间的“死亡谷”,扼杀了无数优秀的科研成果。李飞不甘心:“难道这么好的项目,就只能发篇论文?”
南京医科大学产业合作与转化部部长、苏州南医大创新中心副主任闻洋找到他:“您自己做企业!把成果接下来!”学校组织技术、法务、投资专家团队,对他的专利进行全面市场化评估和价值判断,并为他设计最优转化路径。2023年,苏州缘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成立后,创新中心继续提供公司注册、财务代理、政策申报、人才招聘等一站式孵化服务。
各项支持政策也成为坚实的托举之手。2024年11月,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联合发布《关于在全省开展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改革的通知》,明确鼓励和引导高校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近3年来,南京医科大学也围绕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制定修订涵盖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政产学研平台管理、科研人才评价激励、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十余项制度……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回看李飞科研与创业的来时路,正是这一精神的生动体现。乘着政策“东风”,苏州缘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南京医科大学完成YJ-2301的专利转让,转让金额高达5000万元。“要让以李飞教授为代表的科学家们无后顾之忧,就要帮助他们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他们的论文‘纸’变成‘钱’。”闻洋说。
“企业家”“科学家”的标签一直在李飞身上来回交织。他也清醒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异,科学家的目标是探索未知、发现可能的解决方案;企业家则要从市场出发,快速做出有市场价值的产品,实现盈利,保障团队生存与发展。
如今,他频繁奔波于各大风投、药企之间,一遍遍讲解精心准备的PPT,为YJ-2301项目寻求研发资金。前不久,好消息传来,YJ-2301吸引多家药企洽谈。“一辈子能做成一个创新药,是我们药学科研工作者的终极梦想。既然我有了这个机会,就要全力以赴。”李飞笑意盈盈。
记者手记
一份“执念”背后的托举
“一辈子能做成一个创新药,就是最大的梦想。”李飞的这句话很朴素,却格外打动人。梦想也许遥远,但坚持让它不再虚无。
坚持二字,说来简单,真正做到却难如登天。失败、等待、反复、孤独,几乎是科研人的日常。多少人在一次次碰壁中选择转身,在长久的寂寞里选择放弃。
可偏偏有人,就是愿意用数十年时光去守候那一束微光。李飞教授,就拥有这样的“执念”。
他不断改进化合物结构,寻找更好的药效,或许科学的真谛,就藏在这种咬牙坚持里。创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壮举,而是无数次试错之后仍不愿放弃的执着。
仅有个人的坚持还不足以托起梦想。科研领域长期存在着成果“沉睡”的问题,科研人员有热情,却往往受制于机制的束缚、资金的短缺。
李飞教授是幸运的,他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制度与政策的托举何其重要。正是因为有了鼓励创新的政策指引,有了学校愿意当“翻译官”“保姆”的机制探索,有了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才让科学家的坚守不再只是“孤勇”,而是可以变成落地生根的现实。坚持与托举,就像两股力量,前者点燃梦想,后者托举梦想。缺少任何一方,创新之路都走不远。
科学家的韧性需要被尊重,科研的价值需要被呵护,机制体制的改革需要被持续推进。当这些力量汇聚时,创新才不会是一句空话。